“窃名”者与他们的帮办
说老实话,我并不知道上海有个“当代艺术博物馆”。那天雨下个不停,我去参观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故地——三山会馆,在中山南路下了车,先看到的不是我要找的三山会馆,而是挂得十分显眼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指路牌,顺着牌就望见那个标志性的大烟囱,像一只巨人用的体温计直戳阴霾的天空。
看完三山会馆我寻过去,走着走着忽然就没有了密密麻麻、晾挂衣服的居民楼,像进入了一片妆点一新却停了产的工厂区,下午两、三点,路上已难觅行人,是因为绵绵不断的雨还是没人对小资的心血来潮感兴趣?那通体铁灰色似厂房又似一个冷冰冰的大仓库的建筑立在江边,冷雨中愈显萧瑟,还没走到近旁已感到丝丝凉气。建筑有模仿巴黎蓬皮杜中心的意思,至少是同一个思路——将工业化的丑权当美感复制到本可逃离的物品上,但少了前者的俏皮,蓬皮杜中心时刻在提醒观望它的人:我不过是一个故意开的玩笑。模仿者忘了一点,故意开的玩笑,以其特别,第一个做的人可以以新鲜的理由强词夺理,接着做的人,就不是丑的创造,而是丑的复制了。工业化去人性的一面,时常留在它的生产地,城市里消费享受的人群凭著本能逃避著那份冷酷,但有一种自命的“艺术”说:我不让你们逃跑,我要恶心你们。这种“艺术”就是所谓的“当代艺术”。
待我进了馆,第一感觉是空,因空而大。在城市房价绑架了所有人的今天,这里却在提醒走进来的人空间可以不是钱,空间可以毫无意义,甚至“空”本身就是“当代”的,它不求充实、不求美感,只要随意——自订的自由。
空而大对人的心灵并无损害,只是让它有一种漂浮感,而人建博物馆、把前人或别人的精神创造罗列进去,寻求的恰恰是一种归属和附着感。这就是“当代艺术”生之孽源,它注定是活不下去的,它的存在注定只能像个骗局。
既然只能以骗局的形式存在,目的就变得非常重要,而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恰恰是没有目的的,或者是不需要目的的。人之创造唯艺术是不需要目的的,赚钱也好,妆点也罢,都是附加的目的,艺术于人只是一种愉悦。不能给人愉悦的“艺术”,只剩下时间和目的,“当代”这个头衔不过是与时间耍了个花招,为其目的服务的,它的真实代号是“时政”。既然只剩下目的,那目的必然是野心勃勃的,还有什么比政治更能帮挺没有艺术的艺术。其实“当代”这抢在历史前面的定义,预示著这个组织的临时性,因为“当代艺术”是先有组织后有个体、先有概念后有作为,“当代艺术”四个字,“当代”才是主角,“艺术”只是追着概念的玩伴。这针对目标物搭建的突击队性质的组织,只在特定社会或政治框架内才被赋予意义,离开这个组织的价值流水线,单作为个体的创作它是没有意义的。
我在空大到人愈显渺小的展厅里,撞见形单影只、只手可数的参观者,他们都是同类型的年轻人,约摸三十岁上下,不太修边幅但并不忽略时尚的那种,估计多是读了书从了艺不必用两只手直接糊口的人。我喜欢转博物馆,除了个别只吸引特定人群的小博物馆,构架如此之阔大、名头也不小又能这么安静的,唯此一家,人少亦不杂。可看的也实在不多,时常几十平米的空间只存放一件展品。展品一般需靠专门的文字说明来喻意,欣赏的人是被解说引进门的,一上来眼睛就被缴械了,事实上审美的确是多余的,基本是凭借文字侵入大脑作用想象力去诠释一件物品或一些画面,非此眼前的均可视为垃圾,因为无用亦无美感。生活中没有这两个作用的东西可不就是废物和垃圾,然而一班人在文字解说的循循诱导下,围着废物反复琢磨,努力要让“不知所云”变作“宣言”。我只知道在过往的世纪,有人能将“宣言”变成“不知所云”,还不知道人类又向前迈了一大步,连编带蒙已能将“不知所云”变作“宣言”。
主展在五层,一个叫“中国当代艺术奖 ”(CCAA)的组织正在办十五周年回顾展,占了整层楼,好不风光。CCAA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自然是一定要标榜“独立”的,这两个字已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就没有人想一想瑞士这弹丸小国的前大使(CCAA的创办者)从哪儿来的能耐创办这个组织?这个没有工厂大烟囱金钱却滚滚而来的山地小国是世界统治集团贵族们的“老巢”,所以才能没有工业化的污染却富得流油,所以才能数百年免于战火,全是落不到中国人头上的不可解释的“奇迹”。我走了这么远,鬼影般跟在身后的就是雪一样融化的奇迹,一个接一个。它们连成一条线,清晰地分开了那些好运和倒楣的民族,只在这条隐而不露的线上,你可以琢磨出命好和命坏所由何来。
展馆的宣传录影上专门提到创办者出于“谦虚”没有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了“中国”这个首码为他在华一手策划的当代艺术奖冠名。从这段特意的介绍看,中国人(博物馆的管理者)受宠若惊,因为人家作为创办者本可将该组织命名为“某某当代艺术奖”,但却慷慨地命名为“中国当代艺术奖”。
我看了这段录影,欲哭无泪,欲笑不能,卑贱者在卑贱的路上走得太久,魂灵一路丢失已找不回来,连赠与窃都分不清,不知“绿林好汉”乃“江湖大盗”,台前变一变“独立”“非赢利”的魔术,就一举将“中国当代艺术”的名头窃走了,在某些被点了穴的国人的感激涕零中,不费吹灰之力“窃了他人之国”。凭哪一条就这么让他们代表中国?就凭他们纠集的这班模仿者又如何能代表中国?关键之关键,为什么要由他们调兵遣卒代表中国?一国之审美权和道义权,就这么一个转身即被劫入囊中,还伴随着被劫者的“荣耀”。
作者:边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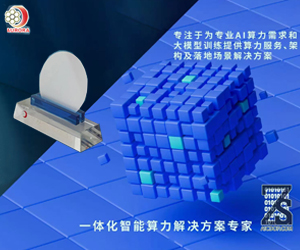




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