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河西,天人合一—漫谈季羡林的东方文化观
引子
2014年3月,我与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先生在北大书法研究所作了一次关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身份的学术对谈。这次对谈的部分内容经《中国艺术报》记者何瑞捐(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场记录整理,以一个整版的版面在《中国艺术报》理论版刊出。报纸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中国戏曲学会的秘书长万素同志是我多年的笔友。她在看过此对谈后,于4月1日给我发来短信:“访谈已拜读,学术价值甚高!我们会组织学习,引发更多学者思考,将您和王教授的理念向更广阔的空间推广。正像你们文中极力推介费(孝通)季(羡林)学术思想那样。这项工作需要更多有识之士通力合作,您已率先发动起来。”
万素同志发来短信的时候,我正在法国参加太湖文化论坛2014巴黎会议。她告诉我中国戏曲学会顾问刘厚生先生建议她将此文列印分发该会各位领导学习参考。厚生老是近百岁的老人了,是一位我敬仰的老前辈,不仅学问深厚,为人也境界高尚。去年还为我主持的《中国艺术报》撰写关于中国戏曲现状与前途的长篇理论文章,引起戏曲界的思想“地震”。这样一位戏曲理论界的学术泰斗能关注和首肯我和岳川先生的文化学术对谈,当然是令人感动的。
因为我和岳川先生谈的是文化身份,必然谈及文化自觉、21世纪、北京大学等等,其中我提到自己与季羡林先生的交往。孰不知,岳川先生说他曾给季先生做过8年的学术助手!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的共鸣、共识就更多了,话题也越说越热烈,一时间把当时在场的北京大学的博士们和青年学生都感染了。当时他们就评价这是一场精彩的学术对话。
那时,我就觉得我应该写写我对季羡林先生的认识。因为他曾经在一篇重要的文章中提到我的名字。我与他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关联,如果不写点什麼,实在是有愧于先生,虽然这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
我与季羡林
事情是这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正在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文化报》任理论部主任。因为是一张文化报纸,又做着理论评论工作,我当时是大力提倡并努力践行用文化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经济、艺术、文学等等一切问题。记得还主张和开设过“从文化看”这样的栏目,也曾经从文化角度与着名科学家、经济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探讨他们各自领域的深度话题。平日里读书买书,也是见了“文化”字样就有佔有和阅读的欲望。
大概是1993年初,季羡林先生在新出版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天人合一”新解》。这篇文章将中国文化的价值导向和精神高度引向“天人合一”,提出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发展方向和模式,并且大胆预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天下,东西方文化在21世纪将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并且是规律性地引发东方文化掘起,因为文化发展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这篇文章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经历了一波“文化热”后的文化界、文艺界均引起轩然大波。他那仿佛是非学术性的话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更是引发激辩。我记得当时国内一家着名报纸就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做标题报导季羡林先生的观点和引起的争议。
那时候季先生的散文写作还没有到随后的井喷之时,文名并不见大传,学界以外知者不多。但是他是北京大学着名文化学者,是东方文化学、印度学、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着名学者,已经享誉文革后正在复苏的学术界。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传统文化热(包括文学界的寻根热)中,随着北京大学文化书院的创办和传统文化讲座的开办及随之產生的巨大影响,季先生在其中已是十分活跃和中坚性的学术名人。记得大概是1993年年中某时,《中国文化报》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话题,由我们理论部承办,召开了几次学界名人的座谈会。我们邀请了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王朝闻、刘开渠等等学术界、文艺界的老专家。那时,他们都是些耄耋老人了。所以,我们都是一个一个地接送他们。我就是负责接送张岱年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两位老人和蔼可亲,朴实朴素。我在与季先生聊天时谈了我对他的《“天人合一”新解》的读后感,也将我听到的反响和议论转述给了他。其时,我并不太在意,祗是因为他如此支援报社工作甚为感念,同时作为编辑也想通过交流拉近与作者的感情和距离。所以,此前是研读了季先生的作品和新近着述的。不料想,这也促成了他的新作问世。1993年9月19日,季羡林又写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长文《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全面丰富了自己的前述思想。这“两论”成为季老文化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之后被收入几十种文集之中。在这篇“再思考”中,季老提到了我的名字。他开篇时写到:“今年春天,我在新创刊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天人合一’新解》(以下简称《新解》),阐述了我最近对东西文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想法,大概仍然属于野狐禪之类。不意竟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剑虹、向云驹等先生相告)。同时,我自己也进一步读了一些书。我并无意专门搜集这一方面的资料,资料好像是自己跃入我的眼中。一经看到,眼明心亮。我自己也有点吃惊:资料原来竟这样多呀!这些资料逼迫我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柴剑虹是当时的中华书局编辑。我们俩的反馈被季老特别提及,看来是相当重视和认真记取了。
但是,季先生的观点在当时那个世纪之末,国家、国人普遍关心中国经济发展,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际,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和趋势性并没有佔有它应有的社会位置,季先生如此预测中国或东方文化的世纪之变,确是空谷足音。他的文化预言不同于过去有过的夜朗自大式的传统、守旧、自恋的“自我夸张”,他是站在他那个时代的最前沿,採取了当时最新鲜的多样而丰富的材料来说明、论证、支撑自己的观点,并且以远大的眼光和宏大的视野预见并预言未来。他指出:“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由于这一表述使用了中国民间的一个俗语,仿佛将一个严肃的科学的严谨的话题变成了“戏说”,于是至今仍为人议论。季老对此心知肚明:“我引的这两句话,最受人詬病,然而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真理,是詬病不掉的。”可见,他是相当自信和自负的。
严苛的学术训练
季老是学术中人。照我的看法,他是一个有相当文化自觉的学术大家,他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并且一向擅长考据之学。他所做出的学术结论,是有学术境界、学术思想、学术方法的。许多人误认季老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非学术、民间语、宿命论,其实谬也。
我们不妨看看季老的学术背景和他的学术习惯。
出言谨慎是他的重要学术教训。在留法十年中,为博士论文“导论”事,让季先生终身铭记。我不妨照抄他的一段自述:
我现在讲一讲“导论”(Einleitung)的问题。论文主体完成以后,我想利用导论来向教授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我穷数月之力,翻阅了大量的专着和杂志,搜集有关混合梵文的资料以及佛典由俗语逐渐梵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说法。大学图书馆就在印度研究所对面,借书非常方便,兼之德国人素以细緻、彻底、效率高闻名世界,即使借一本平常几乎没有人借阅的古旧的杂志都不用等很长时间,唾手可得。这也给我提供了写作的便利。结果写成一篇洋洋万言的“导论”,面面俱到,巨细不遗,把应该或者不太应该、祗有点沾亲带故的问题,都一一加以论列。写完以后,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沾沾自喜,把全部论文请Irmgard Meyer小姐用打字机打好,等到Waldschmidt休假时,亲自呈送给他,满以为他会大大地把自己褒奖一番的。然而,事与愿违。过了几天,他把我叫了去,并没有生气,祗是面带笑容地把论文稿子交给了我。对其餘部分他大概还是非常满意的,祗是我的心肝宝贝,那一篇“导论”却一字未动,祗在文前面画了一个前括弧,在最后画了一个后括弧,意思很明显,就是统统删掉。这完全出乎我期望,几乎一棍子把我打晕。他慢慢地对我解释说:“你讨论这个问题,面面俱到。其实哪一面也不够充实、坚牢。人家如果想攻击你,什麼地方都能下手,你是防不胜防!”他用了“攻击”这个字眼,我至今忆念不忘。我猛然省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这一“棒喝”,把“导论”一概不要,又重新写了一篇相当短而扎实得多的“导论”,就是现在出版的这一篇。在留德十年中,我当然从这位大师那里学习了不少的本领、不少的招数,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一篇“导论”,我终生难忘。以后,我教我的学生时也经常向他们讲这个故事。写学术论文,千万不要多说废话,最好能够做到每一句话都有根据。我最佩服的中外两个大学者Heinrich Lüders和陈寅恪就是半句废话也不说的典范。(《治学生涯•博士论文》)
他后来在一篇回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治学经验的文章中,再一次表述了自己当时的震惊:“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写规模比较大的学术论文,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剧烈的打击。然而我感激这一次打击,它使我终生头脑能够比较清醒。”
有过如此这般学术经历和学术训练,我们可以确信季先生的学问是有原则和底线的。
深厚的国学传承
国学大师传承的学统对他有深刻影响。2007年,季先生出版了他的新作集《病榻杂记》,其中“廓清”文字中提出了三辞:一辞“国学大师”,二辞“学界(术)泰斗”,三辞“国宝”。一时间,又是举世瞩目。他谦称自己不配这些社会封来的种种头衔、桂冠,“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先生是极清醒、极有自知之明的人。他要辞掉的“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都是他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文化界日益活跃,并与他“放言”河东河西而声名日隆有关。虽然他本人坚辞这些“桂冠”,但并不是说他于国学一无用心,或无足轻重。他的国学情结和学术成就我们可以看这些材料:
1.胡适与陈寅恪的评价与影响。季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德十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99年5月,季先生访台后写了一篇文章《站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文中他表示:“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胡适是其中之一。“二战”后,季从德国回国,就是因为在德国给陈寅恪写有一信并寄出自己若干论文文章,得陈赏识,陈表示可以推荐季到北京大学工作,并表示要向胡适(校长)、傅斯年(代理校长)、汤用彤(文学院长)一一写信。陈在国内学术界一言九鼎,他的赏识与推荐是很有份量的。果然,季顺利回国并就职于北京大学,并且获得副教授职,一週后任教授。并组建与出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此后便与胡适接触日多。胡适对季的信任和使用令季感念不忘。此间,季羡林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浮屠与佛》,一篇《列子与佛典》。前篇被陈寅恪讚赏并推荐给当时最有学术影响和权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后篇他给胡适看过,胡看后第二天便致信季,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这一评价让季终生不忘。几十年后,季到台湾,李亦园先生告季,适之先生晚年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胡先生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先生对此写道:“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我的学术研究。”胡适逝世二十多年后,虽然在文革中胡适是被批判的最大的学界对象,但季先生是第一个公开写文章重评胡适的学人,后来他还承担了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的主编工作,并为其作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序,取其副题为“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胡适先生做学问有一句最着名的缄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本人也是一个学贯东西的学者。这些是不是对季羡林的“河东河西”说有潜在而巨大的影响呢?1989年,季老在40年后,继《涂屠与佛》之后,续写文章《再谈“涂屠”与“佛”》,认为自己解决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心中极喜”。他说:“原来看似极大胆的假设竟然得到了证实,心中颇沾沾自喜,对自己的研究更增强了信心。觉得自己的假设确够‘大胆’,而‘求证’则极为小心。”
对季羡林做学问最有影响或最有直接影响的是陈寅恪。除了前述陈对季的发现、培养、赏识、推荐外,早在清华大学期间,学习西洋文学的季羡林还旁听了陈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课,随其学习《六祖坛经》和佛学,从此与佛学佛典、佛经翻译、中印文化研究结下不解之缘。正是陈寅恪的赏识和推荐,才有了季的留德而归,才有了他的北大60多年的学术与教学生涯,才有了他的教授、系主任等种种职衔,才有了他的佛学影响和学术精进。季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回忆陈寅恪先生》,1995年)我认为,陈寅恪先生取人是绝对唯学术的。季先生留洋十年,既精德、英语文,又通印度文献,熟研吐火罗文、梵语等绝学,对佛学不隔,于汉学有母语优势,还师从过国内外诸多名家大师。这不是人才是什麼?看看季先生晚年80多万字的《糖史》就知寅恪先生的眼力有多精凖。所以,季先生的“河东河西”说是学人之语,不可能没有深意存焉!
2.季先生论学范围和学术领域。提出“河东河西”说时,季先生已入晚年,积累了一辈子的学术成就,在诸多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这样的学人怎麼会“胡言乱语”呢?我们看看他的治学领域。他自己说:“我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约有如下几项:⑴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⑵吐火罗文;⑶印度古代文学;⑷印度佛教史;⑸中国佛教史;⑹中亚佛教史;⑺糖史;⑻中印文化交流史;⑼中外文化交流史;⑽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⑾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⑿德国及西方文学;⒀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⒁散文及杂文创作”。
他的学问如此广博,而且其中无论西学、中学、印度学都是国际国内着名学者为其师授。比如留德十年中,他的德国老师都是一流的学者,他跟随他们亦步亦趋接受了最严格、最严谨的学术训练和培养,并且是这些老师所欣赏的优秀学生。有些老师不惜以耄耋之年向季作倾身授受,把自己的绝学绝术绝招传之于他,使之得以继往圣之绝学。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既长期浸淫西学之中,又对东方印度、中国文化有深刻理解的学人,实属凤毛麟角。所以,一些惊俗骇世之说的提出,是必须有奇人方能出其奇语的。季先生的“河东河西说”盖入此类乎?
3.他还有更广大的学术视域。越至晚年,季先生的学术视野越日益广大,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文化课题和命题。这些思考、研究、问题,如果一一展开,都涉及学术史的颠覆和人类文化走向的改弦更张。“河东河西说”是其中的一个子项而已。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个别问题是如何建构在宏大思考之中,是有大问题、大视野作支撑的。他一向自认为拙于理论(义理),长于考据,但晚年却越来越深涉义理之中。我以为这是一个常有思想、勤于思考的学人,日经月累、长年积累后的学术必然。材料所见如此丰富,思考渐至百川汇海之境,大道理、大义理、大理论、大哲学、大学问是必然呼之欲出。
学贯中西,然后才能明辨中西
1997年,季羡林说:“我想到的问题很多。这几年在许多文章中和座谈会上,我都讲到过。约略言之,可以有以下诸端,性质不同,但都与东西方文化有某些关联: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国有的术语,採用同西方不同的判断方法,这样才能在国际学坛上发出声音。第五,中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第六,我认为,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则是综合的。第七,西方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征服’手段是错误的;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正确的。第八,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为世界人民谋福利的同时,產生了眾多的弊端甚至灾害。现在如仍不悬崖勒马,则人类生存的前途必受到威胁。第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切还仅仅祗能算是犖犖大者。你看,这些重重怪论,累累奇思,怎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我这个半瓶醋岂非过分狂妄不自量力了吗?我决无意哗眾取宠。我多年的胡思乱想让我不得不写。不管别人如何骇怪,我则深信不疑。”
季先生在这里列出了九条大项,可以说件件都是大课题、大学问。把这些课题解决好了,也就是重建中国文化、文学、语言、文艺理论、美学、历史、哲学、科学技术的现代体系、现代话语、现代格局、现代价值的面貌,重新解读中国传统。这种重写、重读、重释、重建,不是把原始的传统原封不动地复原、回归、重现,也不是按西方话语体系改造、改变、改写中国传统,而是在瞭解东方传统、深諳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的文化“自新”,走的是一条全新的文化路线。
比如,他说:“研究汉语的专家们的那一套分析汉语语法的方式,我总认为是受了研究西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方法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一条路最终是会走不通的。汉语有时显得有点模糊,但是,妙就妙在模糊上。”
比如,他说:“按西方语言,‘美学’这个词儿的词源与人的感官(Sense Organ)有关。人的感官一般说有五个,即眼、耳、鼻、舌、身。中国和印度等国都是这样说。可是西方学家却祗讲两官,即眼与耳。美术、绘画、雕塑、建筑等属于前者,音乐属于后者。这种说法实际上也可归入常识。可是,中国的美学家忘记了,中国的‘美’同西方不一样。从词源学上讲,《说文》:‘美,羊大也。’羊大了肉好吃,就称之为‘美’。这既不属于眼,也不属于耳,而是属于舌头,加上一点鼻子,鼻子能嗅到香味。我们现在口头上时时都在讲‘美酒’‘美味佳餚’等等,还有‘美食城’这样的饭店。这些在西方都不能用‘美’字来表述。西方的‘美’不包括舌头和鼻子。祗要稍稍想一想,就能够明白。中国学者讲美学,而不讲中国的‘美’,岂非咄咄怪事!我说,这是让西方学者带进了误区……美学必须彻底转型,决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而必须大破大立,另起炉灶。”
比如,他说:“我们传统的文艺理论,特别是所使用的‘话语’,其基础是我在上面提到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与植根于分析的思维模式的西方文艺理论不同。我们面对艺术作品,包括绘画、书法、诗文等等,不像西方文艺理论家那样,把作品拿过来肌掰理分,割成小块块,然后用分析的‘话语’把自己的意见表述出来。有的竟形成极端复杂的理论体系,看上去令人目炫神摇。……我们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或一般读者,读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篇诗文,先反复玩味,含英咀华,把作品的真精神灿然映照于我们心中,最后用鲜明、生动而又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中国的文艺理论实际上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又派别繁多,议论蜂起的。……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语’,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还在作祟,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腰板挺不直,被外国那一些五花八门的‘理论’弄昏了头脑。……我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多思考,勤试验,在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思想指导下,才能为世界文艺理论开闢一个新天地。”
所以说,季羡林提出“河东河西”说,决不是随意轻意而言,相反是有深言深意的。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来看他这段论述就更加明瞭了,“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东西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本来是两句老生常谈,是老百姓的话,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提出来说明东西文化的关系,国内外都有讚成者,国内外也有反对者,甚至激烈反对者。我窃以为这两句话祗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古代哲学讲变易,佛家讲无常,连辩证法也讲事物时时都在变化中。大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内心,无不证明这两句话的正确。我不过捡来利用而已。《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也不就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吗?”
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放在一起看天下大势,季老是第一人。此中,分合是中国问题、历史问题、时间问题,河东河西是东西问题、中外问题、文化问题、空间问题。我们不能简单说分、合,东、西孰优孰劣,一切都应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现实的时空来观察与判断。这两句古语、俗语是可以在具体的时空中產生出新颖的历史结论的。
曾师从着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驤先生的葛剑雄博士在上世纪80年代末,用全新的历史观重释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与价值,使旧说焕然一新。他在其论文《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中认为,历史上所说的中国不等于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以几个一统王朝存在的年代来统计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上称臣纳贡之类情况十分复杂,此种归属不等于实际上的统一;王朝统治范围之外的政权和地区不等于分裂。历史上的统一或分裂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带来各自的利和弊,往往形成互补和刺激,推动着历史的进程、进步或停滞、退步。比如,在文化上,“统一政权强调文化和思想的统一,推选以儒家学说为主的教育。长期的封建统治和思想灌输使大一统的观念和正统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即使在分裂时期,统治者也无不以正统自居,以恢复统一为号召;非汉族统治者也同样如此。在世界文明大国中,中国是唯一能保持历史的延续、文化的一致和疆域的稳定的国家,这些观念的深入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由于產生的消极影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自由,到近代更成沉重的包袱,也是必须正视的。而在分裂时期,统治者往往无暇旁顾,放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为了增强国力,无不寻求新的学说,任用新人。旧的权威衰弱了,新的权威尚未树立。群雄割据的局面使知识分子可以挑选主子或寻求庇护所,所以有可能出现思想活跃、学术繁荣、人才涌现的局面。”
葛剑雄为此下的结论与季羡林对“河东河西”下的结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历代的统一政权,尤其是清朝的统一,无疑对现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分裂时期的政权或分治、自治的政权也曾发挥过各自的作用。对统一分裂这一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不能採取简单的、图解式的划分,而应该对它们產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过程来加以考察,但不能用今天的标準或西方的标準来作出评价,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事实,尤其不应该脱离中国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中央集权的特点。”葛文对分合的辨析,澄清了中国人的通俗历史观中的误会、误解、误识,对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及分合,以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发展观大有脾益。
季羡林解决的是另一个重要的民间思想观,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问题。
他是先从“天人合一”谈起的,因为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他梳理了“天人合一”命题的来源和含义,介绍了其中的释义分歧,介绍了孔子、子思、孟子、老子、董仲舒、张载以及冯友兰、侯外庐、杨荣国等古今哲学家的种种观点。又集中笔墨介绍和推崇了去世不久的钱穆(宾四)先生的“天人合一”观。季先生特别赞同钱穆对中国思想的评价。他引用了钱的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这是钱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写于1990年5月,先刊于台湾报刊,又在大陆刊于1991年第4期《中国文化》),强调文中的如下观点:一中国思想有与西方态度极相异处;二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③钱表示他是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惜已年老体衰,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唯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四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嚮往之宗主。世界文化从此何所嚮往?今天值得重视此问题;伍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千年不绝,又因中国文化从不违天、不违自然,故此下世界文化之归结,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季先生于钱穆文章心有戚戚焉,故接过来继续言说。他首先指出,“我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次,他认为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二、印度文化;三、从古代希伯莱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四、肇始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者属于东方文化,第四个属于西方文化。
第三,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第四,“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是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
第五,东方文化曾在人类历史上佔过上风,起过主导作用。曾经“三十年河东”,后来西方文化取而代之,最近一百年来是“世界人类文化所宗”,此乃“三十年河西”之谓也。但是,最近50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东方文化应该“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新一轮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目标,是历史的螺旋式上升或“轮回”。
在《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文中,季先生就前文作了大量新材料、新观点的补充、丰富、完善。
他补充了张载关于“天人合一”的论述材料,并证明“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是深入人心的。同时补充了日本、朝鲜(韩国)思想史中的“天人合一”资料,以补充前述中国和印度的材料,构成了更广大的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
他辨析了西方科学主义的弊端。他不讚同那种认为祗有发展科学、技术、经济,才有可能最后解决环境问题的观点。他认为祗顾“发展”,空喊“科学”,以为有朝一日科学会自己找出办法的“那一套科学主义”是绝对靠不住的。“科学绝非万能。”
他坚持认为东西方文化是不同的两种模式,两者不可能无差别的、平分秋色的融合。无论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东西方文化的差别都是显而易见的,是表现在眾多的地方的。东西方文化的起起落落,是此消彼长的,而不是对等的融合,是两个文化发展阶段,前后衔接的融合,是“东风压倒西风”式的。因为一是以分析思维为基础,一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这两种思维方式是不可能对等融合的。其中,中国文化有过印度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明清之际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五四运动三次“输液”,这使得中国文化得以葆其青春;类似的“输液”在西方文化是不明显的,工业革命以后的繁荣阶段,更是根本没有的。“这是东西方文化最显着的区别之一。”“黑格尔用正—反—合这个公式说明事物发展规律。我觉得,在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上应该是正—反—正。”
与时俱进的天人合一
季羡林先生提出“河西河东”说,最早出现在他1989年的文章《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1990年发表的《21世纪:东西方文化的转捩点》再次强调申论他的“河西河东”说。这是此一思想的早期表述,其来源是在一个宏大的视野里和一个世纪转折的时代里发现了问题,提出了新的学术思想观点。可以说这是一个应运而生的命题。当他为此论证中国思想掘起于其最伟大的思想和最有高度的哲学“天人合一”时,后者又必然引申、推导出“河西河东”的结论。两解“天人合一”后,季先生又陆续发表了眾多的文章讨论中西文化和“河西河东”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西方不亮东方亮》《东学西渐与“东化”》《东西文化的互动关系》《拿来和送去》《“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等。不仅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河西河东”学说,而且以“送去主义”为话题,讨论了实现此一学说和文化发展进程的方式方法。
文化的影响力就像老子所说“上善若水”,是水一样地向四处、低处弥漫、传播。文化交流、文化影响,取决于文化达到的高度。没有高度就没有文化传播。季羡林提出的“河东河西”说,核心理念取自于“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精神和境界,取决于这一核心价值观在当今时代的普世价值和理想高度。大概是因为钱穆先生宣导,几乎在文化上与季先生呼应“天人合一”,哲学界一些着名学者也对“天人合一”作了新的哲学詮释,肯定了“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和中国思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哲学界的主流话语是讨论主体性问题。着名学者张世英从自己专长的西方哲学进入到中国哲学,并且从主体性问题中梳理出中西方主客二分和主客不分的流变,对“天人合一”作出了新的哲学解读。1995年,张世英出版了他的哲学研究转折性成果《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在书中他集中思考与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一是哲学何为?他指出:“大体说来,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西方传统哲学是主客二分的哲学。中西哲学史各有其发展线索,中国哲学史是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原则到转向主客二分式的发展史,明清之际是转捩点;西方哲学史是从古希腊早期的主客不分思想到长期以主客二分为主导原则又到现当代反对主客二分的发展史,也可粗略地说是‘天人合一’到主客二分又到‘天人合一’的发展史。”张先生这段话,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下:中国哲学从天人合一到主客二分再到天人合一,西方哲学也是从天人合一到主客二分再到天人合一。其中,中国天人合一历史悠久,思想深刻,传统深厚;西方则在主客二分上佔有更大优势。二者可以互补互鉴,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天人合一,中国经验可发挥更多优势,而中国要实现更有高度的天人合一,又必须充分地完成主客二分的发展。这既揭示了“河西河东”规律,又指出了东西轮回中有螺旋上升的时代性的历史事实。季先生虽然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个性,但他也认同中国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消而化之的史实及其积极意义。他的文化个性观点并不是僵化的、“民族主义”的。
张世英先生由天人合一,引出“西化”“东化”,在某种意义上,与季羡林先生的文化观虽不乏大异其趣之处,但他们共同宣导的都是一种高境界的“天人合一”。张世英说:“中国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给中国人带来了人与物、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高远境界。……中国当前要发展自然科学,需要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固有的形而上的普遍性(统一性、同一性)和确定性很容易同中国儒家传统固有的封建‘天理’的整体性和不变性勾结在一起,从而製造一种新型的加倍压制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哲学。我不讚成西方后现代主义完全否定主体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思想,但针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封建‘天理’的顽固性,后现代主义未尝不可以对我们起一点衝击和振聋发聵的作用。另一方面,西方传统哲学过分强调思与诗、概念与隐喻的划界,把诗排斥在哲学之外,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一些重要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则力图取消这种对立。如果说我们对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召唤叫做‘西化’,那麼西方现当代哲学主张人物交融,提倡诗化哲学,就可以叫做‘东化’。我们为什麼不可以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这种思潮结成联盟呢?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也许是一种既有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进取精神,又有天人合一、人物交融的诗意境界的哲学,是个体性、差异性和流变性从传统的整体性和凝滞性中获得解放的哲学。”显然,这里的“天人合一”,即来自于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理念。
无论是季羡林还是张世英,乃至钱穆等等追摹“天人合一”时,都是指的一种现代意义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有原始的“天人合一”,也有充分发展的“天人合一”。很多人误解中国传统哲学,误解“天人合一”,误解季羡林的文化观,都是缘由于此。
“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普适和普世的价值,既在于它在中国历史上由来有自,普遍地历史地存活于全过程,是历朝历代思想传统中主流的、核心的、可持续的、再传承的价值观,也在于它不仅“普史”,而且“普世”——普天下,即可为人类各异地异族异国带来福祉、福音,具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性,是全人类的共同的思想、精神和理想。祗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了“天人合一”,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真正的意义而不至于被这句民间俚语、俗语、戏说给忽悠了,相反要惊诧于民间语言中的大智慧和大俗中的大雅。也许,这正是季羡林先生为什麼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风险,“野狐谈禪”地、机趣无限地对一个庄严硕大神秘的话题作如此一番“骇人”言说的原因。
文:向云驹
注:本刊独家稿件的所有文字、图片版权,均属本刊专有,如需转载,请载明出处。
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拓展重大新闻的文化张力,提升全球华人的文化自信,欢迎关注《东方文化》微信公众号(ID:dfwh_h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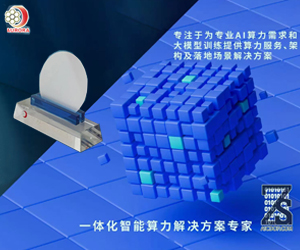




评论已关闭